再思解经错谬 (一): 字义研究上的错谬 (上)
(I) 导论
有者正确说道: “好的解经使人活起来, 荣神益人; 错误的解经却足以扼杀生命, 害己害人.” 卡森(D. A. Carson)[1]所写的《再思解经错谬》, 就是为帮助读者在解经时, 避免犯下书中详细指出的字汇、文法、逻辑、前提和历史方面常见的错谬, 并选取更正确的解经方式, 借此鼓励读者能够更谨慎且忠实地将圣经的原意解明出来.

(II) 五大方面的错谬
卡森(D. A. Carson)在其所著的《再思解经错谬》一书中, 提出了五大方面的解经错误:[2]
- 字义或字汇研究上的错谬(Word-Study Fallacies);
- 文法上的错谬(Grammatical Fallacies);
- 逻辑上的错谬(Logical Fallacies);
- 前提上的错谬(Presuppositional Fallacies);
- 历史上的错谬(Historical Fallacies).
(A) 字义研究上的错谬
文字是奇妙的! 它既能传递资讯, 又能抒发情感, 又是我们用以思考的工具. 字汇(或译“字词、单字”, word)是传道者的基本工具之一 — 不论是他所研究的字词, 或是用来解说他所研究的. 奥斯邦(Grant R. Osborne)贴切指出, 字义研究(word study, 注:《再思解经错谬》将之译作“字汇研究”)已经成为解经最普遍的一个层面. 只要稍微浏览标准的注释书, 就会发现它们多半是用逐字的方式探讨一段经文. 一般大学或神学院的解经课, 也常花很大部分时间在字义研究上. 尽管如此, 我们看到即使是著名的圣经学者, 也可能犯上字义研究方面的错谬. 让我们进一步探讨.
(A.1) 字根的错谬
在所有的错谬中, 解经者最常犯的错谬, 就是假设每个字词的意义与它的字形, 或与它的构成有着密切的关联. 由此观念导出的结论是: 字词的意义乃由语源学(etymology)来界定; 也就是说, 一个字词的意义是由它的字根来决定的. 我们常听到的例子如: (1) 希腊字 apostolos (使徒)的字根是 apostellô (我差遣), 所以“使徒”的意思就是“被差遣的人”; (2) 希腊字 monogenês (独特)的字面意义是“独生”, 就是“独生之子”的意思. 但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英国圣公会牧师兼神学家提瑟顿教授(另译: 田素顿, Prof. Anthony C. Thiselton)曾以英文“nice” (美好的)一字为例, 这字原是由拉丁文“nescius” (无知)演变而来. 但在今天, 当某人说另一个人“nice”时, 我们不会因“nice”的字根意义(指隐藏意义或字面意义)代表“无知”而认为所说的那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无知的.
提瑟顿教授也用 greenhouse 一字作为例子. Green (绿)和 house (屋)各有许多不同的意义, 若将两个放在一起, 就成为 green house (注: 这个词本身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含义不同), 或成为 greenhouse (意即“温室”), 而这两个字原有的意义(即“绿”和“屋”)差不多都不合用了.[3]
语言学家罗沃尔(另译: 鲁欧, J. P. Louw)也提出以下例子来说明这方面的错谬. 保罗曾在 林前4:1描述自己、矶法、亚波罗等为“基督的执事(希腊文: hupêretês ). 圣公会大主教兼诗人特仁赤(另译: 特仁慈, Richard C. Trench)认为 hupêretês 是由动词 eressô (划)演变而来, 所以 hupêretês 最根本的意思应该是“摇桨者”(rower). 罗伯逊(A. T. Robertson)和霍夫曼(J. B. Hofmann)更是推波助澜地认为, 从语形来看(morphologically), hupêretês 是由hupo 和 eretês 结合而成, 推论 eretês 在荷马(Homer, 古希腊诗人)[4]著作中(公元前8世纪)即是指摇桨者; 于是霍夫曼将这字和语形学(或译: 形态学, morphology)相联结, 推断 hupêretês 基本上是“下-摇桨者”(under-rower)、“摇桨副手”(assistant rower)或“附属的摇桨者”(subordinate rower). 特仁赤没有扯这么远, 也没有说 hupo 有任何“从属”的含义. 尽管如此, 澳洲的新约圣经学者莫里斯(Leon Morris)仍推论 hupêretês 为“卑微的仆人”之意; 巴克莱(William Barclay)更是指出 hupêretês 如同“罗马战船上最低层的摇桨者”. 但这些看法仅依据一个可能的特例 — 而且它仅是“可能”, 并非确定.
事实上, 在古典文学著作中, hupêretês 从未用来指“摇桨者”, 新约圣经中也没有这种用法. 正如罗沃尔所评析的, 将 hupêretês 的含意溯自 hupo 和 eretês, 就像将英文字 butterfly (蝴蝶)说成是 butter (奶油)和 fly (飞)结合而成, 或将 pineapple (凤梨)说成是 pine (松)和 apple (苹果)的结合同样滑稽.
回到先前所提到的例子, 希腊字 apostolos (使徒)和其字根 apostellô (我差遣)是否是同源字, 仍然是有争议的. 但在语意的讨论上, 新约经文并不将其意思集中于“被差遣的人”, 而将重点放在“报信者”. 报信者通常是被差遣的, 但报信者涵盖这个人所携带的信息, 并且暗示他是代表那位差遣他的(意即主耶稣的使徒是代表差遣他们的主耶稣). 换言之, 在新约圣经里, apostolos 通常用来表示“特殊的报信者”或“特殊的代表”, 而非指“被差遣的某个人”.
至于希腊字 monogenês (独特), 这字通常被视为由 monos (唯一、独一)加上 gennaô (生产的“生”)衍生而成“独生子”之意. 在语源学上, 希腊字 gen- 的字根相当棘手: monogenês 可以被简单地说成是由 monos (唯一、独一)加上 genos (意即“类”或“族”)而成, 意指“类中独一的”, 意即“独特的”或类似的说法.
虽然 monogenês 在新约圣经里, 通常用来描述孩子和父母的血缘关系(路7:12; 8:42; 9:38), 但我们还是得谨慎界定其用法. 来11:17称以撒为亚伯拉罕的 monogenês (《和合本》译作“独生的儿子”), 但明显其意不是“独生的儿子”, 因亚伯拉罕也生了以实玛利(创16:15-16), 并且也与基土拉生了一群子孙(创25:1-2). 这字在此处的意思应该是“独特的儿子”, 因为以撒确实是亚伯拉罕“独特”的儿子, 是他特别钟爱的. 【编者注: 故有者建议把 约3:16译作: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独一无二(或作: 独特)的儿子赐给他们…” 这样的译文不是为了白话文而改写, 也不是要否认某一基要真理, 而纯粹是为了语言学(linguistics)的理由】
“针对上述的讨论,” 卡森评述道, “我要另外加上三项警告. 首先, 我并不主张每个字词(或译“字汇”, word)可以随便有任何的语意解释. 通常我们可以观察出每个字限定的语意范围(semantic range), 然后根据上下文, 在某种范围内修订或塑成某个字的意义. 但语意范围并不是恒常固定的, 随着时间和用法的改变, 语意也将相形变动.
“即便如此, 我也没有说字义的变动是没有限制的. 我只是强调字词的语意不能单靠字源(etymology)来确定, 或说一旦我们找到某字根的意思, 任何由这字根合并而来的字都会含有类似这字根的意思.[5] 就语言学而论, 语意并非字词本身所具有的. ‘语意表明的是一种集合起来的关系, 其中动词的表征只是一个记号’. 从某方面而言, 我们说‘某字的意思如此如此’是合情合理的, 但这只是在我们以归纳性的观察, 提供字义范围, 或者特别指明在某段上下文中, 某个字词的含义. 但是, 我们绝不能因此过度倚赖语源学的包袱(etymological baggage, 指过度靠语源学来定义).”
其次, 一个字词的意义是有可能反映出其组成部分的意思. 例如, 希腊文 ekballô {G:1544}这个动词是由 ek (出来、出于)加上 ballô (投掷、驱赶、放置)所组成, 它的意思正是“我丢出”、“我掷出”、“我逐出”. 卡森解释道: “一个字可以或可能反映(may reflect)它的语源; 我们得承认这样的情形较常发生在综合性语言中, 如希腊文或德文 — 因着两种语言的字汇和字义有显而易见的关系. 但英语则较隐晦, 它的字词与字义间较没有自然而然的关系. 即使是这样, 我要阐述的是: 我们仍旧不能假定语源和语意是有必然的关系. 我们只能按个别的字词, 经由归纳后所发现的字汇意义来检视.”
“第三,” 卡森继续写道, “我绝对没有暗示语源学的研究是无用的. 语源学是重要的, 例如在研究一些历经时间长河的(diachronic)字词, 或在尝试详细说明这字最原始(最早)的意义, 甚至在研究同源语系(cognate languages), 以及在那些(在新约圣经中)仅仅出现一次的字词(hapax legomena)方面, 语源学是功不可没的. 在辨认字词的语意上, 语源学虽是相当有限的工具, 但由于缺乏其他更有效的方法, 语源学有时就变得别无选择了(即有重要性了).”
正如古巴出生的美国圣经学者史尔瓦(Moises Silva)在其卓越的研究中指出, 语源学对旧约圣经的重要性远胜于新约圣经. 无论如何, 纯粹以语源学作为解明字词语意的基础, 那只能算是一种“具有学术修养的臆测而已”(educated guess).
(A.2) 语意时序的错置
当我们将某字晚期的用法(指这字词后期的意思), 注入早期的著作时, “语意时序的错置”便发生了. 这在相同语言中尤其容易发生, 例如(约主后100-450年)初代教父(the early church fathers)所使用的一些希腊文字词, 其意思就有别于(约主后49-96年)新约作者使用时的意思.[6] 例如, 当初代教父们使用 episkopos (主教, bishop)这希腊字时, 所指的是同时监管数个地方教会的领袖, 但新约作者使用这字时却没有如此含义(注: 这字在新约圣经是指监管一个地方教会的领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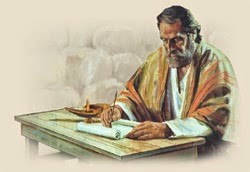
因此, 除了语意上的时序错置以外, “炸药”不足以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也不能使我们成为像祂那样的荣美样式. 当然, 传信息者讲到“炸药”时, 强调的乃是神伟大的能力. 即使如此, 保罗意指的绝不是炸药, 而是空坟墓(意即主复活的大能).
(A.3) 沿用过时的语意
就某方面来说, “沿用过时的语意”这项错谬是上一项错谬(语意时序的错置)的倒影, 即诠释者赋予某个字的语意, 在时间上早已过时(其语意范围早已不存在了).
卡森解释道: “我个人的书架上有一本《过时英语辞典》(Dictionary of Obsolete English), 当然, 书中一些字汇已失去功用, 早已被废置不用(例如: 英文字“to chaffer”意思是“讨价还价、斤斤计较”). 但最棘手的还是那些仍被沿用却改换意义的字词. 在圣经语言中也有类似情况; 例如, 荷马时代的某些用词(Homeric words)早就不出现在《七十士译本》或新约圣经的书卷, 而研究圣经的专家对上述古旧的字汇也没有兴趣. 然而, 一些希伯来文的字汇在不同时期可以用不同的意义; 而有些希腊字在古典希腊文中有某个意思, 但到了新约时代又有另一个意思. 这类情况很容易使粗心大意的解经者陷入这第三种错谬 — 沿用过时的语意.
有些字义的变动是不难掌握的. 时下英文字“martyr”(意即“殉道者”)源自希腊文 martus . 有者追溯 martus 这希腊字的名词及其同源动词的意思之发展, 而这发展通常有以下几个阶段:
- 第一阶段: martus 的意思是在法庭内(或外)提供证据的人.
- 第二阶段: martus 指提供见证和确据的人(例如: 为自己的信仰作见证).
- 第三阶段: martus 意指那些即使在死亡的威胁下仍(勇敢)见证其个人信念的人.
- 第四阶段: martus 指那些以接受死亡来见证其信仰的人.
- 第五阶段: martus 指为某种原因(包括其信念或信仰)而死的人 — 殉道者.
当然, 上述的发展阶段并不见得那么容易分清界限. 在同一时期, martus 可以被某个人解释成其中一种意思, 但却被另一个人解释成另一种意思; 或者, 同一个人对同一个字, 因为上下文的不同(语境不同)而有不同的用法. 在这个论据中, 第三阶段通常发生在法庭内, 这使人联想到第一阶段, 因而构成该字在语意发展上的瓶颈(即难以明确地分清这字包含哪个阶段的意思).
显然, 在《坡旅甲殉道记》(Martyrdom of Polycarp)的1章1节, 以及19章1节(主后2世纪中叶作品)完成时, 第五阶段已经隐约可见. 有标准希腊文辞典主张, 当启示录写成时, 第五阶段已经形成: “当我忠心的 martus (见证人? 殉道者?)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 你还坚守我的名, 没有弃绝我的道”(启2:13).
但上述看法可能不够正确, 因为 启11:7论及两个“见证人”(希腊文: martus )的叙述里, 他们在被杀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见证, 这意味着 martus (见证人)的意义不会超过上述的第三阶段(注: 第三阶段的见证人只是受到死亡的威胁, 并不一定死; 但第四和第五阶段的见证人则是经历了死亡). 因此, 启2:13中的 martus 只是单纯的指“见证人”; 又或者, 在约翰使用 martus 一字时, 此字的语意范围包括了多重的阶段.
简而言之, 某个字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改变它的语意. 现今大部分学者已察觉到希腊文中的“小后缀”(diminutive suffixes; 如英文 duckling [小鸭] 或 booklet [小册子]一字的‘ling’或‘let’, 含有“小”的意思)的功用到了新约书卷写成之时, 已大部分失效了; 所以我们很难以年龄或身量区分希腊字 ho pais (小孩)和 to paidion (孩童). 我们也察觉到许多“完成式词首”(perfective prefixes)已失去部分甚至全部的功用.
从上述讨论看来, 任何的解经若不是以那字在第一世纪“通俗希腊文”的用法来决定, 而是优先以那字在“古典希腊文”的字义来解释, 并以此来界定那字的语意, 我们就有必要质疑这样的解经之正确性. 举个例子, 《今日基督教》月刊 (Christianity Today)曾刊载米凯森夫妇(Berkeley and Alvera Mickelsen)讨论 林前11:2-16时, 他们辩称这段经文的“头”(head, 希腊文: kephalê {G:2776})指的是“源头”(source)或“源始”(origin).
然而, 他们的看法是依据一本简称为LSJ的古典希腊文辞典(Classical Greek Lexicon),[7] 而不是“新约及同时期的通俗希腊文辞典”(New Testament and Hellenistic Greek Lexicon).[8] 关于新约希腊文辞典, 那简称BAGD的《新约希腊文辞典》(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9]就是属于新约及同时期的通俗希腊文辞典. 值得一提的是, 这本被公认为研究新约字义最标准的《新约希腊文辞典》, 在列出有关“头”( kephalê )的各种意思和含义中, 并没有提到kephalê 也可指源头(source)或源始(origin).
(A.4) 诉诸“未知”或“可能性不大”的语意
根据卡森(D. A. Carson), 我们可以继续沿用以上的例子, 作为以下的讨论, 来解明第四个字义研究上的错谬 — 诉诸“未知”或“可能性不大”的语意. 米凯森夫妇引用LSJ (古典希腊文辞典)时, 忽略了LSJ在收集证据时所附加的各项限制. 米凯森夫妇把在LSJ里所提到的 “河流之首(或作: 河流之头)”(head of a river)解释为“河流的源头”(source); 不过在这方面, LSJ所收集和引证的例子是:
- 这“头”一词是复数( kephalai ), 而不是像在 林前11:2-16的单数(kephalê );
- 单数的“头”(kephalê )被用来描述河流时, 指的是河口(而不是“河流的源头”);
- 在LSJ中, 只有一个文献, 把单数的“头”(kephalê )用作源头或源始, 即公元前的《奥菲残片》(Fragmenta Orphicorum, 此乃主前5世纪或更早之作品); 但该文献的准确性仍有许多可疑之处, 例如“其原文并不确定, 且有超过一种翻译, 所以其原意并不明确”.[10]
卡森(D. A. Carson)也正确指出, 虽然在一些新约的暗喻(metaphor)用法中, kephalê (头)一词可有源头之意, 但在考虑和参照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却不是必然指源头; 反之, 在这些例证中, 把 kephalê (头)一词用作“权柄”(authority)之意更为恰当. 很多有关这方面的辞典, 充满了引证古老文献的例证, 都一致表明 kephalê (头)一词的意思是“权柄”(指对某人或某群体有领导之权). 米凯森夫妇(Berkeley and Alvera Mickelsen)以及其他持有相同看法的人, 或许是早期受到比戴尔(Stephen Bedale)的早期文章(指1954年刊登于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的一篇文章)所影响. 无论如何, 重点是米凯森夫妇在解析kephalê (头)这个字义时, 引证“未知”或“可能性不大”之语意, 所以其根据和准确性是不可靠的.[11]
此外, 旧约学者沃尔特·凯泽(另译: 华德凯瑟, Walter C. Kaiser)也曾不只一次地辩称, 林前14:34-35的 nomos (律法)并非指摩西律法, 而是指保罗所驳斥的“拉比诠释和拉比教规”(rabbinic interpretation and rabbinic rules). 林前14:34说: “因为不准他们说话. 他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法(希腊文: nomos )所说的.” 按沃尔特·凯泽的说法, 他认为旧约并没有如此记述, 因此保罗所指的“律法”必定是拉比式的教规.
如此一来, 按照凯泽的观点, 林前14:34并非是保罗在教导“女人要顺服”, 而是保罗想要驳斥对手错误的论点【注: 凯泽认为保罗的对手所提的错误论点(即拉比的诠释和教规)正是第34节所说的: 不准女人在会中说话, 她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法(犹太教拉比的教规)所说的】. 接着, 凯泽认为保罗在 林前14:36所说的, 其实是在提出反驳: “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原文是阳性, 指男人)出来吗? 岂是单临到你们(希腊文: monous, 是阳性字; 而非阴性字, monas )吗?” 换言之, 凯泽认为保罗是在 林前14:34引述其对手的论证之要旨, 像他先前所做的一段(参 林前6:12; 7:1-2), 然后自己才在 林前14:36提出纠正的观点.
上述这样的诠释解经有其魅力, 但却经不起仔细检验. 卡森解释时指出, 第36节的 monous 虽是阳性(男性), 但这并不证明保罗写这段话时只是给哥林多教会的男人, 并问他们是否以为神的道理单临到他们 — 不包括女人. 反之, 它所涉及的对象应该是指那组成教会的男人和女人: 通常在希腊文的用法上, 阳性的复数形式(plural masculine forms)是用来指那不分男女的群体【注: 这就好像当保罗说“弟兄们(brethren, 阳性的复数形式), 你们(阳性)要…”, 保罗在此不单单是对弟兄们说话而已, 当然也包括了姐妹们】
此外, 论到 林前14:36的阳性字 monous (你们), 卡森进一步分析道: “保罗所运用的修辞性问句(rhetorical question, 即 林前14:36: “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 岂是单临到你们吗?”), 其目的在于斥责整个哥林多教会信徒在面对教会课题上的松懈及轻浮; 保罗其实是在驳斥哥林多教会信徒在面对各种课题时的专横独断, 而这种专断态度促使他们脱离其他众教会所共守的做法, 甚至促使他们质疑保罗的使徒权柄.”
卡森如此诠释 monous (阳性字, 意即“你们”, 也可指弟兄和姐妹们)有以下三方面的支持:
- 它使 林前14:34所说“像在圣徒的众教会”这句话变得更有意义; 也就是说, 保罗责备的是哥林多教会的某种做法(practice), 而此做法已使这教会有别于其他众教会(注: 卡森也指出, 从句子结构来看, 林前14:34“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语似乎不应该与 林前14:33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 乃是叫人安静”这句话连在一起; 林前14:34乃是它接下来的那一段争辩之经文[指 林前14:35-38]的起首句).
- 我们所采取的诠释也符合 林前14:37-38: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显然因拥有属灵恩赐而显得傲慢、自我膨胀, 甚至严重到跌入一种危机, 即忽视使徒的权柄! 保罗的论点是: 难道他们(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唯一拥有预言恩赐的群体?(林前14:36). 此外, 真正的属灵恩赐岂不是应该能够辨识使徒保罗所写的就是“主的吩咐”吗?(林前14:37). 如此说来, 第36节和第37-38节这两处的对比, 并不是指哥林多教会“男信徒”和“女信徒”的对比, 而是“哥林多教会的男男女女”和“基督众教会”的对比(林前14:34), 以及“哥林多教会违抗使徒权柄”和“众教会遵守使徒权柄”的对照(林前14:37-38). 换言之, 哥林多众信徒必须学习的是 — 要认清他们不是神话语临到的唯一群体(the only people)【因为神的话语显然也论到众使徒和其他众教会】.
- 哥林多前书中也有其他相似的论证(特别是 林前7:40; 11:16), 都支持卡森在上文的诠释(即 林前14:36的阳性字 monous [你们]是指哥林多教会的男女信徒, 而非仅是男信徒).
卡森正确指出, 如果 林前14:36的用意不是为了排除拉比传统(拉比式教规), 那么 nomos (34节的“正如律法所说”)就不能指拉比传统. 卡森解释道: “现在, 我们正进入目前所讨论的错谬之核心所在. 在某种范围内, nomos 大概可以被视为与‘妥拉’(Torah, 即‘律法书’的希伯来字)同意, 并且‘妥拉’在拉比文学的用法上, 涵盖成文的圣经及口传的传统. 在这种前设的观念下, ‘林前14:34的nomos 是指拉比传统’这一论点似乎可以成立(因‘妥拉’可指口传的拉比传统). 然而, 不容否认的事实是: 虽然保罗的著作中常提到 nomos (律法), 但他从未用 nomos 一字来指拉比传统.”
卡森继续写道: “因此, 凯泽的论点就落入此谬误中 — 诉诸‘可能性不大’的语意, 即保罗不曾使用过的论证观念. 因此, 我们可以这样说: 唯有当其他论点在诠释上都说不过去的时候, 我们才被迫提出新的假设: 即使如此, 我们仍然需要承认这种理论(指凯泽上述的解法)是尝试性的(tentative), 且在语言学上极不确定(uncertain).”
卡森总结道: “无论如何, 林前14:34-38这一段经文不需要走到上述‘不得已’的地步. 我们按上下文就能将这段经文解释得很好, 我们也有充分的其他类似经文来解释, 即34节所谓‘正如律法所说的’其实是引用旧约圣经的原则(principle)而非引句(quotation), 而这里的圣经原则无疑是取自 创2:20-24; 保罗曾在 林前11:8-9、提前2:13沿用同样的原则.”[12]
简之, 上述的讨论旨在点出这第四项解经错谬, 可能因着一些人在解经方面的“智巧”, 使经文意义变得混淆不清; 但这仍旧是一项解经错谬.
(A.5) 草率地引用背景资料
从某个角度而言, 米凯森夫妇(Berkeley and Alvera Mickelsen)的例子, 也可以被列入这个错谬范围内. 但本项错谬所涉及的范围, 要比上一项更为广泛. 换言之, 有些错谬虽然在诉诸背景资料时, 不见得那么妥当, 但它未必涉及前一项错谬.
卡森以他自己曾犯下的错谬为例. 卡森指出, 在他所著的《登山宝训》(The Sermon on the Mount: An Evangelical Exposition of Matthew 5-7)一书中, 以典型的传统护道方法, 企图解释马太所说的山(太5:1), 以及路加所说的平地(路6:17), 两者之间的表面矛盾, 甚至认为山也有许多平坦之地.
在上述书籍出版后, 卡森投入撰写较为专门的马太福音注释; 他那时才体会到希腊文 eis to hodos (“上了山”, 太5:1)很可能不是指主耶稣“上山”、“去到山上”或“到山边”, 而是单纯地指“进入山野”. 有趣的是, 路6:17的 pedinos (平地)一般而言是指山区中的平原. 卡森写道: “这样说来, 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实际上并无表面矛盾. 我早先的著作说明我个人因努力不足而造成解经方面的错谬; 若有什么可作鼓励的, 那就是年岁的增长会让人更加谨慎, 我早先所犯的错误, 渐渐教导我改变原先的想法, 并察觉自己的缺失. 因此, 为自己的错谬作出所谓‘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般的情绪性防卫是不必要的.
(A.6) 平行字句的误用
“Parallelomania”(平行字句的误用)是犹太学者桑德梅尔(另译: 桑德米, Samuel Sandmel)所创的专门术语, 旨在点出许多圣经学者所用的一些令人质疑的对比(parallels)用法. 其中之一就是平行字句的用法 — 学者误以为单由这些字句的平行现象(注: 这里所谓的“字句的平行现象”是指类似相同的字句), 就可以展示一些作品之间彼此观念上的联系, 甚至相互的依赖(指可依赖或采用某作品的字义来解释另一作品中相似的字句之语意, 编者按).

“他们其中一位在曼达派(Mandaean)[14]文学中寻找相似的背景, 另一位则企图在有关埃及智慧之神赫尔梅蒂卡(或译: 赫耳墨特, Hermetica)的著作中寻找答案. 这两部文学作品的著作时间, 都是十分不确定的; 然而, 上述两位学者却将这些在著作时间上不能确定的作品, 与约翰福音序言中的用词硬凑在一块(即用上述两部文学作品的用词, 来解释约翰福音序言中的用词之语意, 但上述两部文学作品的背景和时间很可能与约翰福音相距甚远). 这两位学者都对语言学上所谓的‘对比范式对等’(另译: 排比法, contrastive paradigmatic equivalence)不够敏感, 我将在后面(指第16项错谬, 参下期《家信》)处理这一问题. 这样看来, 吉布森(另译: 纪博逊, Arthur Gibson)对布尔特曼在这方面的严峻批判是对的.”
(A.7) 将语言和思维作无谓的串连
若有人在那些精通语言学的人当中提起《希伯来文与希腊文的思想》(Hebrew Thought Compared with Greek)这本书, 就会立刻引发不满, 因为此书犯上严重错误 — “将语言和思维作无谓的串连”. 这项错误的重点在于: 它先假设语言会限制那些使用该语言者的思想过程, 使他们被迫进入某种特定的思想模式, 使他们的思想与别种语言的思维不同【注: 例如有人主张说, 既然希伯来文的时态(tenses)没有像希腊文的时态那么多样化, 就武断认为希伯来人对时间的观念非常简单, 甚至没有能力分辨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就犯上“将语言和思维作无谓的串连”之错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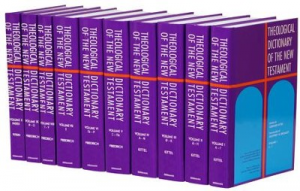
过去这些年来, 这项错谬经常出现在各类学术著作中, 而这问题已被史尔瓦(Moises Silva)作出总括性的整理, 因此不必在此多说. 若有人只是根据字词语意有限的观察而强硬主张“希伯来人的思想是如此如此…”或“希腊人的思想是如此如此…” — 这样的声明是值得怀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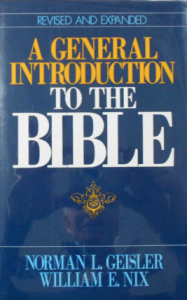
值得留意的是, 一个字词(word)在语法性(gender)方面的“中性”(neuter)并不表示这字就一定没有生命或毫无活力. 我们不能说“阳性”和“阴性”的名词是活泼生动、栩栩如生, 而“中性”(neuter gender)的名词则是没有生命的. 若是如此, 就如卡森所正确指出的, 我们“该如何看待其他语言的中性字, 例如希腊文 to paidion (小子)或德文的 das Mädchen (女子、女孩), 难道这些字不鲜活吗?” 难道这些名词所指的“小子”或“女子”没有生命吗?【注: 上述的“小子”或“女子”肯定是有生命的人, 纵然他们在文法上属中性字】

然而, 我们不能说, 既然希伯来文的动词在文法上只有两种“形态”(或译“体观”, aspects),[18] 那么古代的希伯来人就没有能力辨识过去、现在及未来【注: 若下此定论, 就是将“希伯来人的语言”和“希伯来人的思想”混为一谈, 作出无谓的串连和不正确的结论】.
我们在上文已讨论了“字义研究”(或作“字汇研究”, Word-Study)的错谬中常见的七种错谬. 若合神的旨意, 我们将在下期《家信》继续探讨另外九种字义研究上的错谬.
(文接下期)
******************************
附录: 解经常犯的错谬
卡森(D. A. Carson)在其所写的《再思解经错谬》(Exegetical Fallacies)一书中, 把解经常犯的错谬分成四大类【注: 我们将之改编在《家信》的文章时, 把第四类再分成两部分, 成为第四和第五类】:
- 字义研究或字汇研究上的错谬(Word-Study Fallacies);
- 文法上的错谬(Grammatical Fallacies);
- 逻辑上的错谬(Logical Fallacies);
- 前提上的错谬(Presuppositional Fallacies)和历史上的错谬(Historical Fallacies).
第一类(即字汇或字词研究上)的错谬可分为以下十六种【注: 我们已在上文讨论了首七种错谬】:
- 字根的错谬(The Root Fallacy)
- 语意时序的错置(Semantic Anachronism)
- 沿用过时的语意(Semantic Obsolescence)
- 诉诸“未知”或“可能性不大”的语意(Appeal to Unknown or Unlikely Meaning)
- 草率地引用背景资料(Careless Appeal to Background Material)
- 平行字句的误用(Verbal Parallelomania)
- 将语言和思维作无谓的串连(Linkage of Language and Mentality)
- 对专用语的错误假设(False Assumptions about Technical Meaning)
- 同义字及成分分析的问题(Problems surrounding Synonyms and Componential Analysis)
- 在筛选证据方面的偏执(Selective and Prejudicial Use of Evidence)
- 不当的语意分离与限制(Unwarranted Semantic Disjunctions and Restrictions)
- 不当地限制语意范围(Unwarranted Restriction of the Semantic Field)
- 未经证实就扩充语意的范围(Unwarranted Adoption of an Expanded Semantic Field)
- 希腊文新约圣经及其闪语背景的问题(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Semantic Background o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 未经证实就忽视不同文献的特异用法(Unwarranted Neglect of Distinguishing Peculiarities of a Corpus)
- 未经证实就将“意义”和“指涉对象”混淆(Unwarranted Linking of Sense and Reference)
[1] 唐纳德·A·卡森(另译“卡逊”, Donald A. Carson)是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新约研究教授, 至今撰写或编辑过50多本书, 包括《登山宝训》(The Sermon on the Mount)、《释经的谬误》(Exegetical Fallacies)、《属灵改革的呼召》(A Call to Spiritual Reformation)、《新约解经书概论》(NT Commentary Survey)、《约翰福音注释书》和他得过金奖的著作《上帝的禁制》(The Gagging of God). 他能阅读多种文字, 包括希腊文和法文. 他也是丁道尔圣经研究学社(Tyndale Fellowship for Biblical Research)、圣经文献研究社(Society for Biblical Literature)和圣经研究所(Institute for Biblical Research)的会员.他的专门知识范畴包括历史上的耶稣基督(historical Jesus)、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希腊文法, 以及使徒保罗和约翰的神学. 卡森最初学的是化学(在麦克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取得化学学士学位), 过后改修神学, 在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后去英国深造, 在著名的剑桥大学取得新约博士学位. 1978年参与三一福音神学院工作之前, 曾在三间别的神学院授教. 此外, 卡森也是马来西亚“吉隆坡基督徒会议”(Kuala Lumpur Christian Conference)举办的“巴生谷圣经大会”(Klang Valley Bible Conference)所常邀请的讲员(注: 他在2007年已是第3次成为大会讲员), 其解经常有独到之处.
[2] 值得留意的是, 卡森在其所著的《再思解经错谬》一书中, 只把上述五种错谬分为四种 — 将第四和第五种错谬联合起来, 算为一种(即前提和历史上的错谬).
[3] 奥斯邦著, 刘良淑、李永明合译, 《21世纪基督教释经学 — 释经学螺旋的原理与应用》(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2012年增订版), 第107页.
[4] 荷马(Homer)是约公元前9-8世纪的古希腊吟游盲诗人, 著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其生平及著作情况众说纷纭, 成为“荷马问题”.
[5] 卡森也提醒我们, 不要根据某字根具有某种语意, 而假定或认定这语意也必然会注入较晚期的字义中, 因为字词的意思会因着时间的过去而改变(换言之, 某字在主前第5世纪的意思, 到了主后第5世纪(经过1千年后), 或许其语意会改变. 参《再思解经错谬》, 第33页.
[6] 初代教父(the early church fathers )可分为三个基本的组别: (1) 使徒时代的教父(Apostolic fathers, 主后100年之前的教父, 如: Clement of Rome [主后99年离世] ); (2) 前尼西亚时期的教父(Ante-Nicene church fathers, 主后100年至325年间的教父, 如: Irenaeus、Ignatius、Justin Martyr [约主后165年离世] ); (3) 后尼西亚时期的教父(Post-Nicene church fathers, 主后325年之后的教父, 如: Jerome [主后420年离世]、Augustine [主后430年离世]等等).
[7] LSJ 是古典希腊文辞典 Liddell, Scott & Jones, Greek-English Lexicon的简称.
[8] 希腊文共经过五个主要的阶段: (1) 前荷马阶段 (Pre-Homeric, 主前1000年以前); (2) 古典希腊文阶段 (Classical Greek, 主前1000-主前330年); (3) 通俗希腊文阶段 (Hellenistic或称Koine Greek, 主前330-主后330年); (4) “拜占庭”或称中世纪希腊文阶段 (Byzantine或称Medieval Greek, 主后330-1453年); (5) 现代希腊文阶段 (Modern Greek, 主后1453-现今). 新约希腊文是属于“通俗希腊文”(Hellenistic或称Koine Greek)的阶段, 所以解释新约经文时, 务须参考新约和同时期的通俗希腊文.
[9] W. Bauer,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被 F. W. Arndt 和 F. W. Gingrich 于1975年所翻译; 也被 F. W. Gingrich 和 F. W. Danker 于1979年所修订), 简称BAGD, 是属于新约和同时期的通俗希腊文辞典, 也是研究新约圣经的经文时, 所该优先考虑或查考的标准辞典(其价值[指可靠与准确性]胜于古典希腊文辞典).
[10] 这方面的资料是由卡森的同事所提供, 见 Wayne A. Grudem, Trinity Journal 3(1982): 230.
[11] 希腊文的 kephalê (头)一词与“头权”(headship)和“蒙头”(head-covering)的真理有关; 关于这方面的真理, 请参《家信》文章: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注: 此篇文章进一步说明和证实 哥林多前书第11章的 kephalê 一词含有“权柄”之意】.
[12] 有关“女人在召会中要闭口不言”以及“保罗不许女人讲道”方面, 请参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提前212说不许女人讲道是因为当代女人知识少吗/ ; 也参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4女人的职事/ ; 以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3/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三/ (此篇文章论及有关“男性带领的领导”).
[13] 布尔特曼(另译: 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 1884-1976)是德国的神学家. 他认为新约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借着童贞女所生, 以及所有超自然的神迹、死人复活、圣灵、基督再来等都是神话, 所以他主张“除神话化”才能显出真理的核心. 因此, 他的神学被称为“化解神话神学”(Theology of Demythologization) (参郑国治所著的《神哲学与信仰手册》, 第95页). 这样的神学必须被一切信仰纯正、坚守真道的基督徒所弃绝.
[14] 曼达派(或译: 曼达安教, Mandaean)是一个诺斯底主义宗教, 信仰该教的民族称作“曼达安人”(Mandaean), 其拥有强烈的二元世界观, 崇敬亚当、亚伯、塞特、挪亚、闪姆(Sem)、亚兰以及视施洗约翰为最后一位先知, 并拒绝承认亚伯拉罕、摩西和主耶稣的先知地位. Manda在曼达安语中代表“知识”(knowledge)【注: “诺斯底”(Gnostic)在希腊文也意指“知识”).
[15] 然而, 这并不表示十大册的《新约神学辞典》(TDNT)是完全无用了, 因它仍有不少丰富的字汇背景资料.
[16] 按希腊文法, 性(亦称“语法性”, gender)有三种: 阳性(masculine)、阴性(feminine)、中性(neuter). 但在希伯来文的文法中, 只有阳性和阴性的名词, 没有中性(neuter)名词. 在希伯来文中, 对于没有生命的东西(如椅子), 可以是阳性或阴性, 看字的结构而定. 一般上, 抽象的东西和组词(group)都是阴性词. 【注: 近代有者把希伯来文的“性”分成三种, 即“阳性”、“阴性”和“通性”. “通性”是指不分阳阴, 或阳阴不明, 或有阳有阴, 参 中国的溪水编写组所著的《古希伯来语教程(第1册: 基础篇)》(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年), 第15页】
[17] 例如主耶稣在 太16:19所说的: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按照希腊文法, 这节应该译作: “… 凡你在地上捆绑的, 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 凡你在地上释放的, 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 新约圣经教授基纳尔(Craig S. Keener)写道: “在天上的行动是用‘未来完成时态-被动语态’(future perfect-passive)描写的 — 可以翻译作‘将会是在天上已经捆绑的… 将会是在天上已经释放的.’ 换言之, 地上的判决证实了天上的判决, 是地上的判决根据先前天上的判决(而不是天上跟随地上的判决).” 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天上跟随地上的判决/ . 简之, 希腊文能更精准地分辨事件的时序.
[18] 希伯来文重视动词的“形态”(另译“体观”, aspect)多于它的时态(tense). 希伯来文有两种形态, 就是“完整形态”(perfect aspect, 即放眼于事情的整体全面)和“非完整形态”(future aspect, 较着重于事件的内部结构). 若真的要以时态(tense)来区分的话, 可分为“完成时态”(perfect tense)和“非完成时态”(imperfect tense)两种. “非完成时态”是有点模棱两可, 它既可以代表直说语气(indicative mood, 现在、过去和未来), 也可以代表命令语气(imperative mood)、祈愿/祈使语气(optative mood)等. 值得一提的是, “完成时态”最特出的用法, 就是“先知式的完成时态”(prophetic perfect) — 先知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是如此的有把握, 以致他用“过去时态”来表达(例如: 赛5:13).
Related
作者: 微光
刊登于2022年1-3月份,第132期《家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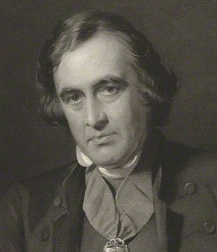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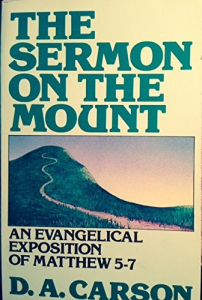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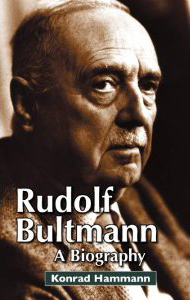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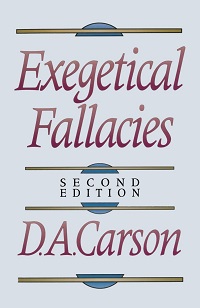

























Leave a Reply